
- 2019年7月10日-12日,上海攬境展覽主辦的2019年藍(lán)鯨國(guó)際標(biāo)簽展、包裝展...[詳情]
2019年藍(lán)鯨標(biāo)簽展_藍(lán)鯨軟包裝展_藍(lán)鯨

- 今日排行
- 本周排行
- 本月排行
- 膠印油墨
- 膠印材料
- 絲印材料
寫(xiě)在中華書(shū)局百年之際:出版物上的追求與貢獻(xiàn)
2012-03-21 09:21 來(lái)源:光明日?qǐng)?bào) 責(zé)編:江佳
- 摘要:
- 一部中華書(shū)局出版史,記載了多少作者、編者、出版者為書(shū)香永駐共同擔(dān)當(dāng)?shù)募言挘粝铝硕嗌贋橹腥A文化薪火相傳相挽前行的剪影。百年中,幾代文化大家,或受聘來(lái)局,或特約著述,將才智乃至畢生心血澆灌中華書(shū)局的繁茂之林。
薪火相傳,我們共同的擔(dān)當(dāng)
一部中華書(shū)局出版史,記載了多少作者、編者、出版者為書(shū)香永駐共同擔(dān)當(dāng)?shù)募言挘粝铝硕嗌贋橹腥A文化薪火相傳相挽前行的剪影。
百年中,幾代文化大家,或受聘來(lái)局,或特約著述,將才智乃至畢生心血澆灌中華書(shū)局的繁茂之林。為作者提供和創(chuàng)造各種寫(xiě)作條件,使一切有真才實(shí)學(xué)的、下過(guò)功夫的作者的著作,都能夠得到出版的機(jī)會(huì),始終是中華書(shū)局編輯們的自覺(jué)。
《辭海》主編舒新城珍藏的毛澤東、惲代英“少年中國(guó)學(xué)會(huì)改組委員會(huì)調(diào)查表”引出當(dāng)年陸費(fèi)逵四處奔走,懇切延請(qǐng)由李大釗等人創(chuàng)辦的“少年中國(guó)學(xué)會(huì)”加盟中華書(shū)局,共同策劃推廣新文化運(yùn)動(dòng)出版物的一段往事。
而編撰者汪朝光寫(xiě)在《中華民國(guó)史》出版之際的一段文字似杜鵑啼血,呈現(xiàn)了為一部傳世著作的出版,作者、編者、出版者的嘔心瀝血:“一部民國(guó)史,做了近40年。實(shí)際上,這也是民國(guó)史學(xué)科從無(wú)到有,從‘險(xiǎn)學(xué)’到‘顯學(xué)’的40年,是民國(guó)史圖書(shū)出版從‘冷門(mén)’到‘熱門(mén)’的40年,更是中國(guó)社會(huì)發(fā)生巨大變遷、學(xué)術(shù)文化界從萬(wàn)馬齊喑到風(fēng)雷激蕩的40年。《中華民國(guó)史》的編纂見(jiàn)證了這一切,也反映了這一切。而這其中,有前輩學(xué)者和出版人的努力,也有年輕一代的付出。40年間,參與編寫(xiě)工作的李新、李宗一、孫思白、姜克夫、彭明、夏良才、周天度、朱宗震等先生已先后逝世,中華書(shū)局參與出版工作的李侃、何雙生等也已離去。”
著名記者、時(shí)事評(píng)論家陶菊隱先生的回憶,則描述了作者與中華書(shū)局間的相濡以沫:“1945年日寇投降后,新城繼續(xù)鼓勵(lì)我修改舊作《六君子傳》,并介紹我到中華圖書(shū)館借閱書(shū)刊,收集有關(guān)資料,以提高其質(zhì)量。中華圖書(shū)館所藏書(shū)報(bào)甚多,我去借閱時(shí),管理人樓、陳諸公給了我很大的便利,深為感幸。《六君子傳》脫稿后,我又繼續(xù)前往收集資料,寫(xiě)成《督軍團(tuán)傳》、《蔣百里傳》等書(shū),均承中華編輯所審閱出版。”
如今已是著名學(xué)者的袁行霈先生,向記者講述了心中的珍藏:1963年,時(shí)任中華書(shū)局總經(jīng)理兼總編輯的金燦然向他約寫(xiě)“知識(shí)叢書(shū)”中《陶淵明》書(shū)稿。當(dāng)時(shí)27歲的他,只是北大一名青年教師。書(shū)稿寫(xiě)作蹉跎。先是政治運(yùn)動(dòng)的干擾,后則因追求完美的寫(xiě)作,直到2000年,袁行霈將《陶淵明集箋注》書(shū)稿交給中華書(shū)局,才了了一樁心愿。“數(shù)十年中,書(shū)局的編輯從未催促過(guò)我,只是關(guān)注著我,不斷送來(lái)書(shū)局的稿紙。中華書(shū)局一直都有這樣的傳統(tǒng),對(duì)年輕的學(xué)者很扶持,而且能體諒作者的艱辛。”學(xué)者安作璋的感動(dòng)同樣持久:“初稿寄回來(lái)修改,除了邊頁(yè)上寫(xiě)的鉛筆字和各種符號(hào)不算,單是粘在書(shū)稿里面的寬窄不等的大小紙條就有80余條,每條上都密密麻麻地寫(xiě)滿了蠅頭小字。這些都是有關(guān)修改意見(jiàn)和應(yīng)注意的問(wèn)題。”
不斷生長(zhǎng)的記憶,接起百年歲月,續(xù)寫(xiě)著中華書(shū)局與她的作者之間一個(gè)世紀(jì)的學(xué)術(shù)情誼。
“……因?yàn)闆](méi)有禮堂,也沒(méi)有較大的會(huì)議室,每次全體職工大會(huì)就在小院的天井里開(kāi),人們有的坐在臺(tái)階上,有的搬個(gè)凳子坐在角落里,有的坐在窗臺(tái)上。一眼望去,不是禿頭頂、長(zhǎng)胡須,就是駝背腰。青年人簡(jiǎn)直寥寥可數(shù)。”后來(lái)?yè)?dān)任中華書(shū)局總編輯的李侃記錄的是1958年中華書(shū)局重組之時(shí)的境況。
為組建一支勝任古籍整理出版使命的編輯隊(duì)伍,金燦然忍辱負(fù)重。他奔走于書(shū)局與北大之間,推進(jìn)古籍整理人才培養(yǎng),參與教學(xué)方案制定,延攬專題課教師,調(diào)撥圖書(shū)資料,“通知我們到中國(guó)書(shū)店的書(shū)庫(kù)里挑書(shū),書(shū)款統(tǒng)由中華書(shū)局結(jié)算。此后,中華書(shū)局每出一種新書(shū),都寄贈(zèng)本專業(yè)圖書(shū)室。”時(shí)任北大古典文獻(xiàn)專業(yè)副主任的陰法魯教授曾回憶說(shuō)。
學(xué)校培養(yǎng)難解人才缺乏燃眉之急。金燦然又以過(guò)人的膽識(shí)提出“人棄我取,乘時(shí)進(jìn)用”,不拘一格招徠人才和學(xué)術(shù)權(quán)威,陸續(xù)調(diào)進(jìn)了錯(cuò)劃為“右派”的近二十人,發(fā)配到蘭州大學(xué)的北大教授楊伯峻便是其中之一。“中華書(shū)局接到我《論語(yǔ)譯注》清稿后,交童第德審查并任責(zé)編。當(dāng)時(shí),出右派分子的著作,自是大膽!”
讓楊伯峻沒(méi)想到的是,此后,金燦然又頗費(fèi)周折將他由蘭州大學(xué)調(diào)入中華書(shū)局,為此還挨了批評(píng)。
一部中華書(shū)局出版史,記載了多少作者、編者、出版者為書(shū)香永駐共同擔(dān)當(dāng)?shù)募言挘粝铝硕嗌贋橹腥A文化薪火相傳相挽前行的剪影。
百年中,幾代文化大家,或受聘來(lái)局,或特約著述,將才智乃至畢生心血澆灌中華書(shū)局的繁茂之林。為作者提供和創(chuàng)造各種寫(xiě)作條件,使一切有真才實(shí)學(xué)的、下過(guò)功夫的作者的著作,都能夠得到出版的機(jī)會(huì),始終是中華書(shū)局編輯們的自覺(jué)。
《辭海》主編舒新城珍藏的毛澤東、惲代英“少年中國(guó)學(xué)會(huì)改組委員會(huì)調(diào)查表”引出當(dāng)年陸費(fèi)逵四處奔走,懇切延請(qǐng)由李大釗等人創(chuàng)辦的“少年中國(guó)學(xué)會(huì)”加盟中華書(shū)局,共同策劃推廣新文化運(yùn)動(dòng)出版物的一段往事。
而編撰者汪朝光寫(xiě)在《中華民國(guó)史》出版之際的一段文字似杜鵑啼血,呈現(xiàn)了為一部傳世著作的出版,作者、編者、出版者的嘔心瀝血:“一部民國(guó)史,做了近40年。實(shí)際上,這也是民國(guó)史學(xué)科從無(wú)到有,從‘險(xiǎn)學(xué)’到‘顯學(xué)’的40年,是民國(guó)史圖書(shū)出版從‘冷門(mén)’到‘熱門(mén)’的40年,更是中國(guó)社會(huì)發(fā)生巨大變遷、學(xué)術(shù)文化界從萬(wàn)馬齊喑到風(fēng)雷激蕩的40年。《中華民國(guó)史》的編纂見(jiàn)證了這一切,也反映了這一切。而這其中,有前輩學(xué)者和出版人的努力,也有年輕一代的付出。40年間,參與編寫(xiě)工作的李新、李宗一、孫思白、姜克夫、彭明、夏良才、周天度、朱宗震等先生已先后逝世,中華書(shū)局參與出版工作的李侃、何雙生等也已離去。”
著名記者、時(shí)事評(píng)論家陶菊隱先生的回憶,則描述了作者與中華書(shū)局間的相濡以沫:“1945年日寇投降后,新城繼續(xù)鼓勵(lì)我修改舊作《六君子傳》,并介紹我到中華圖書(shū)館借閱書(shū)刊,收集有關(guān)資料,以提高其質(zhì)量。中華圖書(shū)館所藏書(shū)報(bào)甚多,我去借閱時(shí),管理人樓、陳諸公給了我很大的便利,深為感幸。《六君子傳》脫稿后,我又繼續(xù)前往收集資料,寫(xiě)成《督軍團(tuán)傳》、《蔣百里傳》等書(shū),均承中華編輯所審閱出版。”
如今已是著名學(xué)者的袁行霈先生,向記者講述了心中的珍藏:1963年,時(shí)任中華書(shū)局總經(jīng)理兼總編輯的金燦然向他約寫(xiě)“知識(shí)叢書(shū)”中《陶淵明》書(shū)稿。當(dāng)時(shí)27歲的他,只是北大一名青年教師。書(shū)稿寫(xiě)作蹉跎。先是政治運(yùn)動(dòng)的干擾,后則因追求完美的寫(xiě)作,直到2000年,袁行霈將《陶淵明集箋注》書(shū)稿交給中華書(shū)局,才了了一樁心愿。“數(shù)十年中,書(shū)局的編輯從未催促過(guò)我,只是關(guān)注著我,不斷送來(lái)書(shū)局的稿紙。中華書(shū)局一直都有這樣的傳統(tǒng),對(duì)年輕的學(xué)者很扶持,而且能體諒作者的艱辛。”學(xué)者安作璋的感動(dòng)同樣持久:“初稿寄回來(lái)修改,除了邊頁(yè)上寫(xiě)的鉛筆字和各種符號(hào)不算,單是粘在書(shū)稿里面的寬窄不等的大小紙條就有80余條,每條上都密密麻麻地寫(xiě)滿了蠅頭小字。這些都是有關(guān)修改意見(jiàn)和應(yīng)注意的問(wèn)題。”
不斷生長(zhǎng)的記憶,接起百年歲月,續(xù)寫(xiě)著中華書(shū)局與她的作者之間一個(gè)世紀(jì)的學(xué)術(shù)情誼。
“……因?yàn)闆](méi)有禮堂,也沒(méi)有較大的會(huì)議室,每次全體職工大會(huì)就在小院的天井里開(kāi),人們有的坐在臺(tái)階上,有的搬個(gè)凳子坐在角落里,有的坐在窗臺(tái)上。一眼望去,不是禿頭頂、長(zhǎng)胡須,就是駝背腰。青年人簡(jiǎn)直寥寥可數(shù)。”后來(lái)?yè)?dān)任中華書(shū)局總編輯的李侃記錄的是1958年中華書(shū)局重組之時(shí)的境況。
為組建一支勝任古籍整理出版使命的編輯隊(duì)伍,金燦然忍辱負(fù)重。他奔走于書(shū)局與北大之間,推進(jìn)古籍整理人才培養(yǎng),參與教學(xué)方案制定,延攬專題課教師,調(diào)撥圖書(shū)資料,“通知我們到中國(guó)書(shū)店的書(shū)庫(kù)里挑書(shū),書(shū)款統(tǒng)由中華書(shū)局結(jié)算。此后,中華書(shū)局每出一種新書(shū),都寄贈(zèng)本專業(yè)圖書(shū)室。”時(shí)任北大古典文獻(xiàn)專業(yè)副主任的陰法魯教授曾回憶說(shuō)。
學(xué)校培養(yǎng)難解人才缺乏燃眉之急。金燦然又以過(guò)人的膽識(shí)提出“人棄我取,乘時(shí)進(jìn)用”,不拘一格招徠人才和學(xué)術(shù)權(quán)威,陸續(xù)調(diào)進(jìn)了錯(cuò)劃為“右派”的近二十人,發(fā)配到蘭州大學(xué)的北大教授楊伯峻便是其中之一。“中華書(shū)局接到我《論語(yǔ)譯注》清稿后,交童第德審查并任責(zé)編。當(dāng)時(shí),出右派分子的著作,自是大膽!”
讓楊伯峻沒(méi)想到的是,此后,金燦然又頗費(fèi)周折將他由蘭州大學(xué)調(diào)入中華書(shū)局,為此還挨了批評(píng)。
-
 相關(guān)新聞:
相關(guān)新聞: - ·??????????????????? 2012.01.04
- ·中華書(shū)局:歲月有波瀾 書(shū)香無(wú)間斷 2011.12.30
- ·出版三巨頭商討回歸落戶上海事宜 2011.12.14
- ·書(shū)展調(diào)查:購(gòu)買文學(xué)類書(shū)籍占65% 2011.08.24
- 關(guān)于我們|聯(lián)系方式|誠(chéng)聘英才|幫助中心|意見(jiàn)反饋|版權(quán)聲明|媒體秀|渠道代理
- 滬ICP備18018458號(hào)-3法律支持:上海市富蘭德林律師事務(wù)所
- Copyright © 2019上海印搜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:18816622098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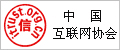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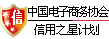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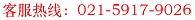









意商城news.jpg)






 主站蜘蛛池模板:
万州区|
盐山县|
大化|
科尔|
阿城市|
永泰县|
云安县|
蒙山县|
灵寿县|
荣昌县|
濮阳县|
萝北县|
青河县|
安陆市|
苏尼特左旗|
永兴县|
泰宁县|
三亚市|
石林|
长宁区|
军事|
米泉市|
固阳县|
磐石市|
蓬莱市|
罗山县|
宿松县|
米林县|
昌乐县|
凉山|
仁化县|
海城市|
芜湖市|
门源|
论坛|
舟曲县|
千阳县|
周至县|
兴国县|
灵丘县|
永宁县|
主站蜘蛛池模板:
万州区|
盐山县|
大化|
科尔|
阿城市|
永泰县|
云安县|
蒙山县|
灵寿县|
荣昌县|
濮阳县|
萝北县|
青河县|
安陆市|
苏尼特左旗|
永兴县|
泰宁县|
三亚市|
石林|
长宁区|
军事|
米泉市|
固阳县|
磐石市|
蓬莱市|
罗山县|
宿松县|
米林县|
昌乐县|
凉山|
仁化县|
海城市|
芜湖市|
门源|
论坛|
舟曲县|
千阳县|
周至县|
兴国县|
灵丘县|
永宁县|